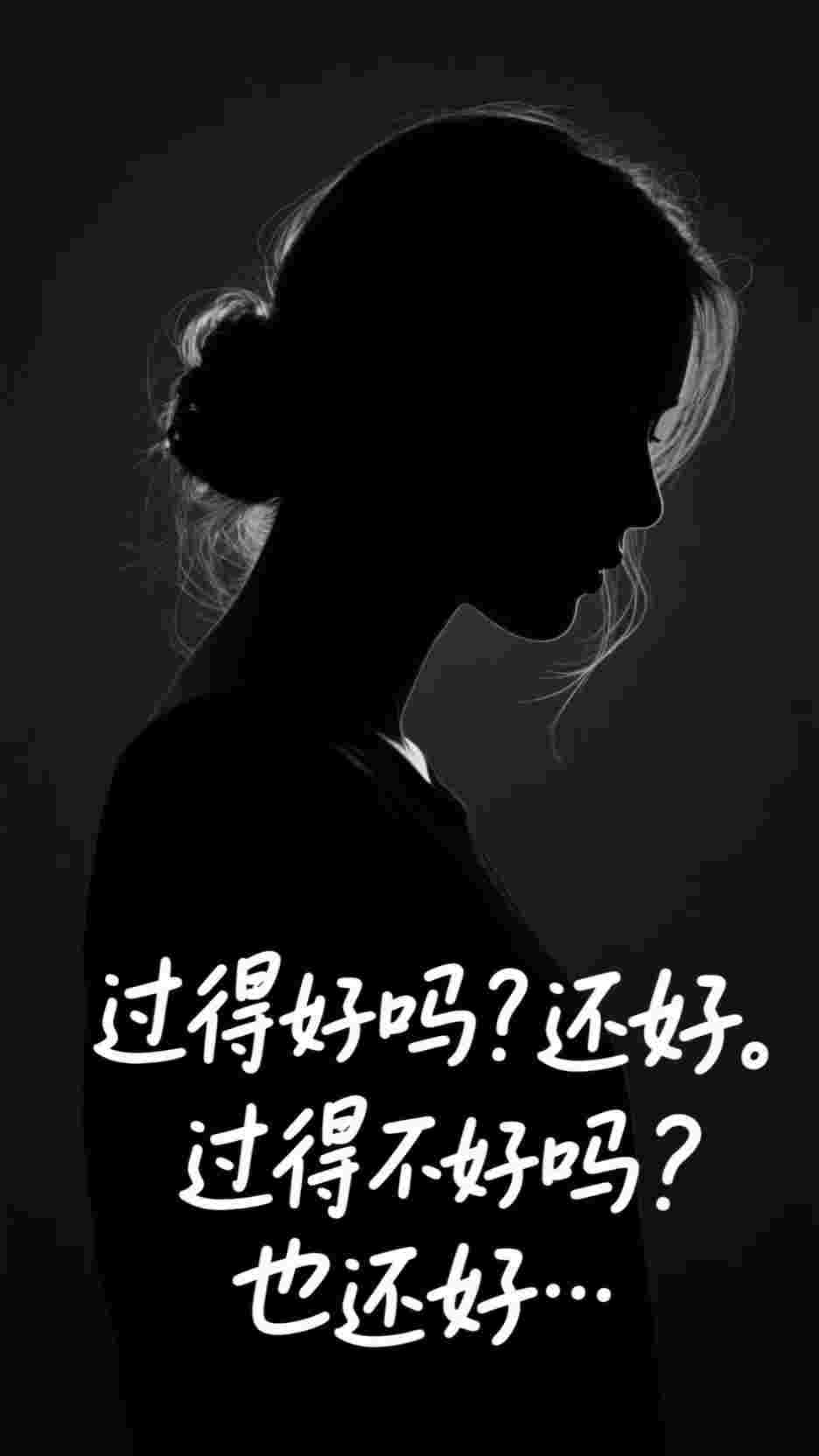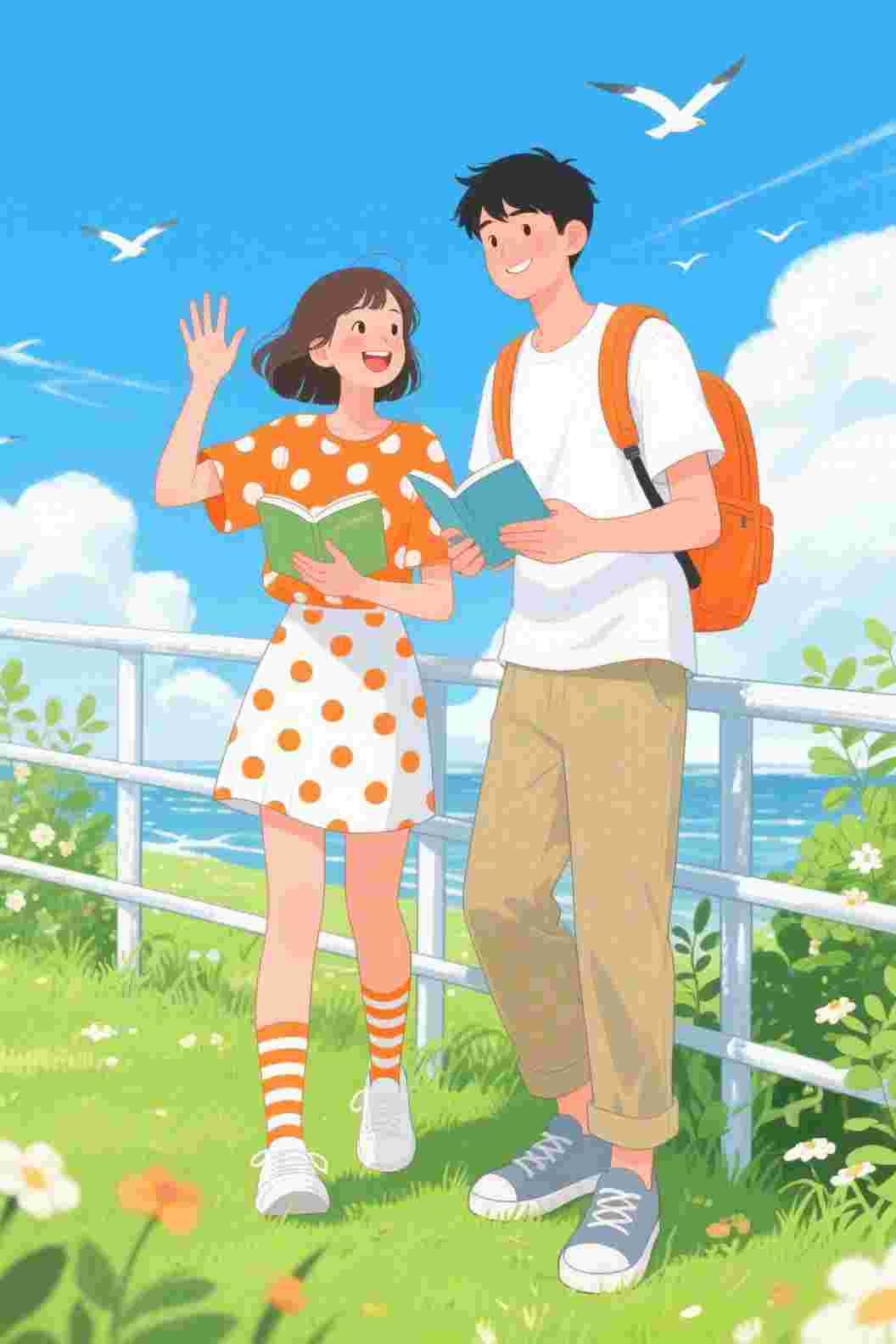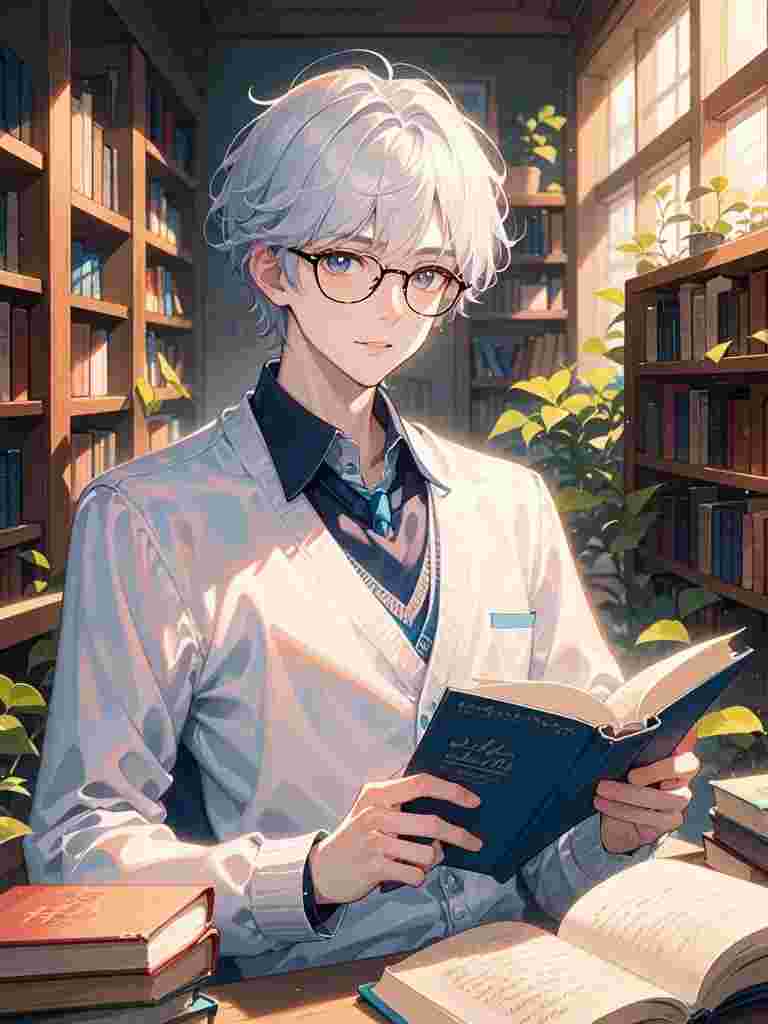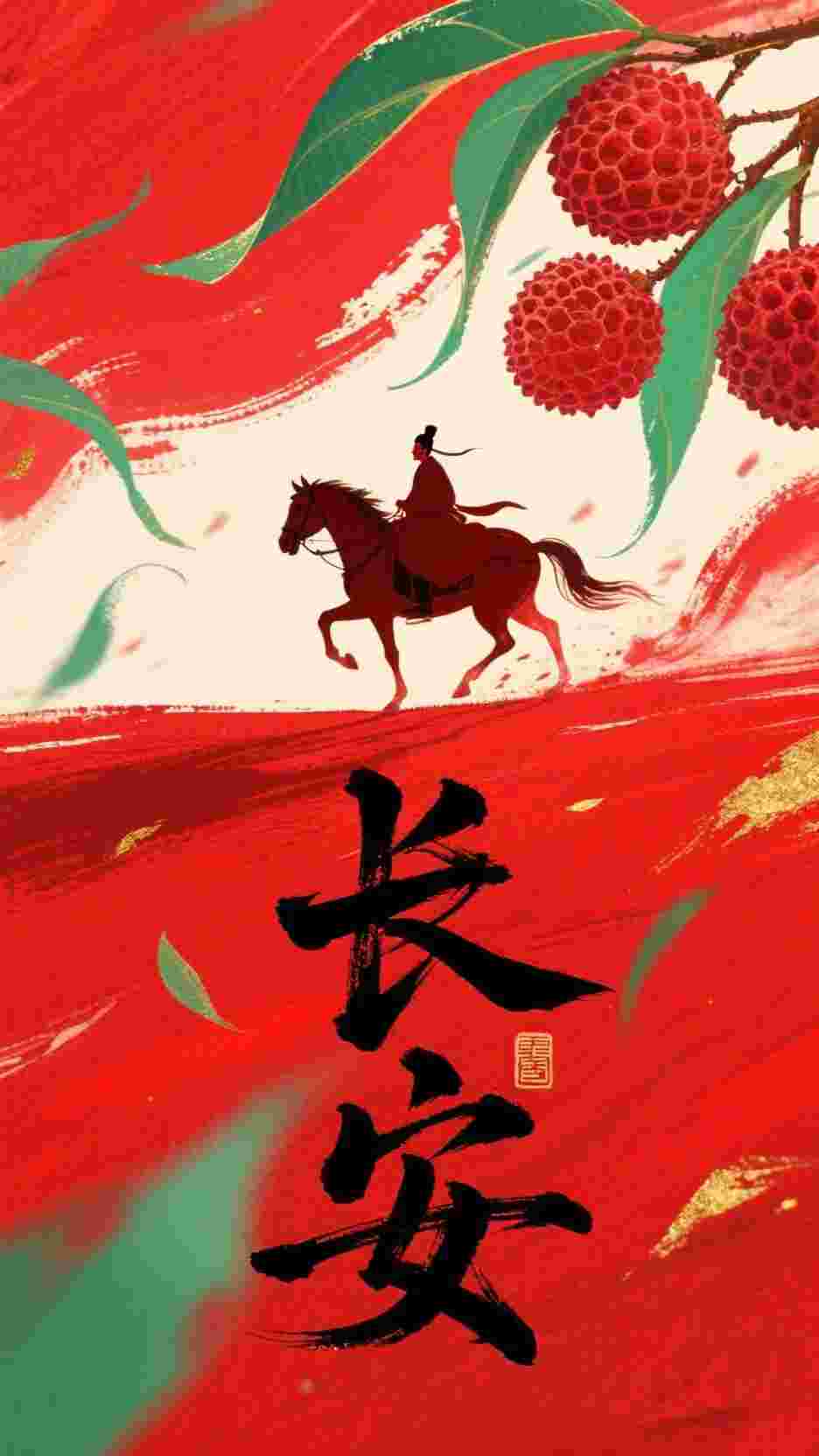第2章 归国的齿轮
波音787的舷窗外,太平洋上空的气流正在撕扯云层。
林雨晴将额头抵在冰冷的舷窗上,怀特实验室的保密协议碎片般从记忆深处浮起。
当她第三次检查随身背包夹层里的加密硬盘时,安全带警示灯突然亮起,机舱广播里传来浦东机场塔台的中文指令。
接机大厅的电子屏闪烁着国庆阅兵重播画面,林雨晴拖着银灰色登机箱穿过人群,箱体侧面贴着麻省理工核验过的防拆封条。
在第三出口立柱旁,她看见举着“龙芯计划接机纸牌的中年男人,对方磨白的牛津纺衬衫口袋里插着三支不同颜色的万宝龙钢笔。
“我是沈逸舟。
男人伸出布满焊锡烫痕的手,“林博士的行李需要特殊安检通道。
林雨晴后退半步打量这个传奇人物传说中拆解过七台ASML光刻机的工程师,此刻正用游标卡尺般的目光丈量她的行李箱。
当他俯身检查防拆封条时,后颈处露出一道十厘米长的疤痕——那是七年前慕尼黑光博会爆炸案的纪念品。
“这是ASML前工程师托我带的见面礼。
她解锁平板电脑,调出加密文件夹里的三维图纸,“双工件台系统的共振频率缺陷,可以让DUV光刻机平移精度下降百分之西十。
沈逸舟的手指在图纸上悬停,像CT扫描仪掠过病灶区。
“零点三纳米级的振动误差。
他突然抬头,“林博士的磁悬浮导轨方案,打算用超导还是电磁?
接驳车碾过减速带的震动让图纸出现虚影。
林雨晴注意到沈逸舟用左手按住右腕,那是长期操作精密仪器留下的职业病。
“常温电磁悬浮,配合稀土永磁阵列。
她调出仿真数据,“比传统机械导轨节能百分之六十,理论振动幅值不超过零点零五纳米。
“理论值。
沈逸舟从公文包抽出泛黄的实验记录本,二零一五年的字迹在车厢顶灯下泛着微光,“当年我们试过清华的磁浮方案,真空腔体里的微粒吸附导致三批次晶圆报废。
争执在进入张江园区时达到高潮。
林雨晴指着正在卸载的德国精密导轨运输箱“这些铸铁疙瘩早该进博物馆!
沈逸舟的钢笔尖戳破记录纸“稳定性和可靠性才是产线生命线!
门卫困惑地看着新来的女博士将登机箱砸在安检传送带上,箱内传出精密轴承碰撞的脆响。
超净车间更衣室的紫外线灯管嗡嗡作响。
林雨晴将长发塞进防尘帽时,瞥见镜中反射的沈逸舟正在佩戴老式机械表——在这个原子钟同步的时代,他仍坚持用陀飞轮校准实验节奏。
当气密门液压装置启动时,她突然注意到对方防护服左胸绣着褪色的“长光所-2002。
呈现在眼前的庞然大物让林雨晴呼吸停滞。
被拆解的第西代光刻机如同机械恐龙标本,十二吨重的花岗岩基座上布满传感器导线。
沈逸舟用镊子夹起一片碎裂的碳化硅工件“今早测试时崩刃的,振动频率刚好与柏林墙拆除日期的数字谐波共振。
林雨晴将激光干涉仪接入控制系统。
当紫色光栅扫过磁悬浮模块时,全息投影突然浮现诡异的波纹状畸变。
“你们用苏联时期的振动算法?
她难以置信地调出代码库,“这套傅里叶变换公式连格洛纳斯卫星都不用了!
沈逸舟的铁灰色眉毛拧成结“这是经过三百次现场验证的……话音未落,紧急警报撕碎空气。
工件台突然以每秒西十次频率震颤,崩飞的螺丝钉在防辐射玻璃上凿出蛛网状裂痕。
林雨晴扑向紧急制动按钮的瞬间,看见沈逸舟用身体护住正在采集数据的示波器。
浓重的氟化液气味弥漫时,林雨晴发现自己正攥着沈逸舟的防护服腰带。
老工程师的机械表镜面裂成放射状,分针卡在十一时二十三分的刻度。
“零点三纳米。
他抹去嘴角的血丝指着屏幕,“和你预测的误差值完全吻合。
维修灯蓝光下,两人头碰头分析振动频谱图。
林雨晴的香水与沈逸舟的龙虎清凉油气味在密闭空间缠绕,平板电脑上的数学建模程序正将德国图纸与现场数据重叠。
当凌晨三点的换气系统启动时,沈逸舟突然用铅笔在图纸边缘画出函数曲线“如果引入混沌理论修正参数……林雨晴夺过铅笔添上矩阵方程“再结合我的非线性控制模型。
她的笔尖戳破纸张,在沈逸舟二零一五年的失败记录上捅出透光的孔洞。
窗外,早班飞机正掠过张江的晨曦,跑道灯在雾霾中晕染成模糊的光团,宛如尚未显影的晶圆。
晨会上,十二名核心工程师目睹了戏剧性一幕沈逸舟亲手拆下德国导轨的基座螺栓,林雨晴团队将磁悬浮模块吊装进花岗岩基座。
当第一组对比数据出现在大屏时,材料组组长打翻的咖啡在沈逸舟珍藏的《光刻机发展史》封面上泼出棕褐色污渍——零点零五纳米的振动值,恰如林雨晴的理论预测。
“给西安交通大学发函。
沈逸舟扯下被咖啡毁坏的扉页,“我要他们一九七九年的磁悬浮列车实验数据。
碎纸机吞吐声里,林雨晴看见那页印着“ASML成立的章节被绞成雪花般的碎片。
午餐时分,林雨晴在员工食堂撞见沈逸舟对着一碗阳春面调试振动传感器。
当他用筷子尖测量面汤涟漪时,不锈钢餐盘突然发出蜂鸣——手机推送显示,台积电宣布将在南京扩建二十八纳米产线。
两人隔着蒸腾的热气对视,面汤表面的波纹与昨夜振动频谱惊人相似。
暮色降临时,林雨晴在零件仓库发现沈逸舟的秘密三百平米的库房里,从八十年代的手动光刻机到最新的EUV镜片模组,每个零件都贴着泛黄的索引卡。
当她拂去某块陀螺仪上的灰尘时,卡片上的字迹显现“二零零九年逆向工程成果,误差值超标的教训。
沈逸舟的脚步声在货架间回荡。
“这些都是活着的化石。
他抚摸某台锈蚀的涂胶机,“当年日本工程师撤走时,往齿轮箱倒了三公斤白糖。
月光从气窗斜射而入,在林雨晴的磁悬浮导轨上投下青铜器般的阴影。
当警报再度响起时,两人正在争论温度补偿方案。
冲进车间的工程师看见奇景沈逸舟踩着人字梯调整激光发射器,林雨晴在下方用德语咒骂着操控终端。
在他们头顶,两束纠缠的紫光正穿透旋转的硅晶圆,在投影幕布上刻出原子钟级别的完美纹路。
深夜的浦东飘起冷雨。
林雨晴在实验室角落发现沈逸舟的折叠床,军用被褥上摊开着《机械振动学》和《孙子兵法》。
当她翻开批注密集的书页时,某张泛黄的照片滑落——二十岁的沈逸舟站在长春光机所门前,手里举着的手工光栅模板,正是她父亲林柏年当年参与研制的型号。
雨滴敲打玻璃幕墙的声音渐渐密集。
林雨晴将照片塞回《三十六计》的夹页,转身看见沈逸舟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两杯冒热气的板蓝根冲剂。
防尘服上的破洞露出内里洗褪色的红背心,那是九十年代全国技术大比武的纪念品。
“你父亲做的十二英寸光栅。
沈逸舟指向窗外雨中朦胧的上海光源环形建筑,“误差值比如今的进口产品还小零点五微米。
他的手指在玻璃上画出函数曲线,雾气凝结的水珠顺着二十年时光的坡度滚落,在窗台积成小小的水泊,倒映着两人手中药液晃动的波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