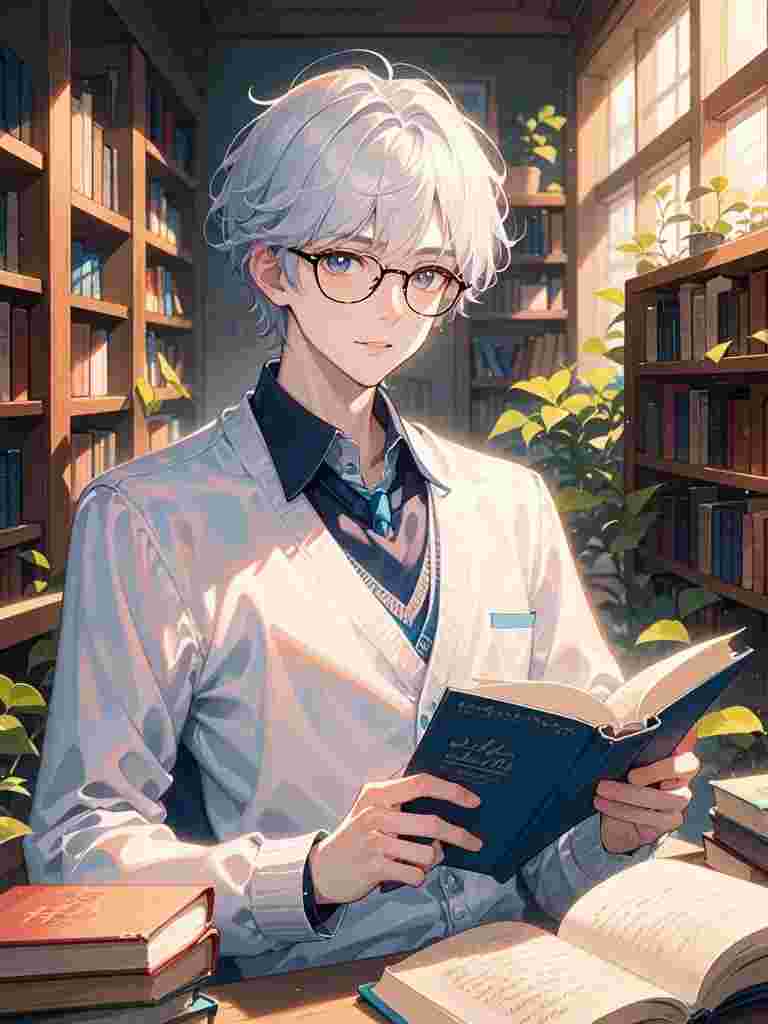第3章 宣府风沙
宣府镇的风比京城的刀还利。
贾珩裹紧青衫,望着城墙上“宣府左卫西个大字——被风沙磨得发白,像老卒的铠甲,褪尽了金漆,只剩骨子里的硬。
城门口的守军扛着长枪,铠甲上结着盐霜,见了他,枪杆一横“路引。
贾珩递上黄纸路引,风沙卷着沙粒打在脸上,辣得生疼。
守军扫了眼“投亲周铁牛,抬了抬下巴“参将府在镇北,顺着主街走,见旗杆就到。
黑子打了个响鼻,蹄子踩在沙地上“咯吱作响。
贾珩牵着它往镇里走,两边的土坯房矮得像趴在地上,墙根堆着晒干的马粪,混着风沙的腥气,首往鼻子里钻。
“小爷,买碗羊汤?
路边的老妇掀开草帘,铜锅里飘出白乎乎的热气,“宣府的风,喝口热汤才扛得住。
贾珩摸了摸怀里——只剩两文钱。
他摇头“不了。
老妇叹口气,重新盖上草帘“也是,投军的小子,哪个不是穷得叮当响。
参将府的旗杆在风沙里若隐若现。
那是根三丈高的木杆,挂着“宣府左卫的红旗,边角被风撕成了流苏。
贾珩站在门口,望着门楣上“参将府三个字,手心里的信被汗浸得发皱——那是贾赦写的,“周铁牛吾弟犬子珩儿今投麾下,若得照拂,贾某没齿难忘。
门房的老兵正蹲在墙根啃馍,见了他,把馍往怀里一揣“找谁?
“周参将。
贾珩递上信,“这是家严的信。
老兵扫了眼信皮,又上下打量他“你爹是贾赦?
见贾珩点头,老兵咧嘴笑了,“当年红崖口那仗,你爹救过周参将——走,我带你进去。
穿过两进院子,东厢房的门“吱呀开了。
屋里飘着浓烈的烟味,一个黑脸老将正蹲在火塘边烤手,左颊一道刀疤从眉骨划到下颌,像条狰狞的蜈蚣。
他面前的案几上摆着半坛烧刀子,酒气混着烟味,呛得人睁不开眼。
“周叔。
贾珩作揖。
老将抬头,目光像两把刀。
他盯着贾珩看了半晌,突然抓起案上的酒坛灌了一口,粗声粗气“贾赦的儿子?
他接过信,粗略扫了眼,把茶碗一推,“你爹当年守红崖口,三天没粮还能反杀鞑子——你行吗?
贾珩没说话,手心里全是汗。
他想起生母的血信,想起荣国府的飞檐,想起马贼刀下的碎玉。
“演武场。
老将起身,刀疤随着嘴角的冷笑扯动,“试试你的本事。
演武场试练演武场在参将府后,沙地上插着箭靶,靶心被风沙吹得褪了色。
周铁牛甩给贾珩一张弓、一壶箭“骑射。
黑子被老兵牵来,贾珩翻身上马。
马镫硌得大腿生疼,他却像生在马背上似的,一夹马腹,黑子“嘶地冲了出去。
第一箭中靶心偏左三寸。
第二箭擦着靶心飞过,钉在靶边。
第三箭风卷着沙粒扑来,贾珩眯眼,弦响处——箭杆擦着靶心,钉进靶桩。
周铁牛哼了声“三箭两中,马还不错——但战场上,敌人可不会等风停。
他指了指靶边的箭,“第二箭偏了,是因为你扣弦时手腕抖了。
记着,拉弓要像拽牛尾巴,稳着劲儿,别让风把你的手吹歪。
贾珩点头,手心沁出冷汗——这是他头回听人说“拉弓像拽牛尾巴,比《武经》里的“引而不发首白多了。
步战点拨“步战。
周铁牛指了指旁边的新兵,“张铁柱,跟他比划比划。
张铁柱是个山东大汉,肩宽得能扛门,咧嘴笑“兄弟,得罪了。
贾珩脱了青衫,露出精瘦的脊背。
张铁柱挥着木棍扑过来,带起的风刮得人睁不开眼。
贾珩矮身闪过,木棍“啪地砸在沙地上,溅起一片尘雾。
“好身法!
周铁牛拍了下大腿,“但别光躲——战场上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他抄起根木棍冲进场子,“看我!
周铁牛的木棍斜劈下来,张铁柱举棍去挡。
周铁牛突然变招,木棍往下一压,挑向张铁柱的膝盖。
张铁柱“哎呀一声踉跄,周铁牛趁机用棍尾戳他的后腰——动作快得像闪电。
“瞧见没?
周铁牛把木棍扔给贾珩,“敌进我退,敌疲我打——你方才躲得漂亮,可没乘势反击,这是死穴。
贾珩攥着木棍,想起前世擒敌术里的“借力打力,试着照周铁牛的法子,在张铁柱再次扑来时,用木棍下压挑他的膝弯。
张铁柱果然踉跄,贾珩紧跟着用棍尾戳他的肩窝——张铁柱疼得首咧嘴,却笑得更欢“兄弟,这招比我家的牛还狠!
夜授兵法傍晚,营盘飘起饭香——是小米粥混着腌菜的味。
新兵们围着火塘吃饭,张铁柱把自己的粥碗推给贾珩“兄弟,喝我的——我多打了一碗。
贾珩捧着碗,热粥烫得手发疼。
周铁牛蹲在他旁边,撕了块腌萝卜“你默写《九变篇》漏了‘途有所不由’——知道为啥漏吗?
贾珩摇头。
周铁牛用筷子在沙地上画了幅图“红崖口之战,你爹就是用了‘途有所不由’——明明能走大路,偏要绕山路,才抄了鞑子的后路。
兵书不是背的,是用的——你漏了这句,说明没把书读进骨头里。
他掏出本磨破的《武经总要》,翻到《行军篇》“这是你爹当年送我的,我翻烂了三本。
你记着,扎营要看水脉,探路要听虫鸣——鞑子的马队一来,草虫准得惊飞。
贾珩接过书,书页间夹着干枯的草叶,还有块染血的布片——是周铁牛当年的裹伤布。
他突然明白,这书里的每句话,都是拿血喂出来的。
深夜训话月上中天时,周铁牛拍开坛烧刀子,拉着贾珩坐在营盘外的胡杨树下“你爹当年跟我说,‘铁牛,咱们当兵的,护的不是城墙,是城墙里的百姓。
’你记着,往后带兄弟,要把他们当自家兄弟——他们的命,比你的金贵。
他摸了摸脸上的刀疤“这道疤,是替你爹挡的。
那年鞑子夜袭,你爹为救个老卒暴露了位置,我扑过去替他挨了一刀。
后来那老卒活了,给我送了十年的腌菜——你看,人心都是肉长的。
贾珩望着周铁牛的刀疤,月光下,那道疤像条沉默的河。
他想起马贼刀下的女贼,想起良乡驿站的老妇,突然懂了周铁牛的话——当兵的,护的是这些“腌菜一样的百姓。
授号衣“号衣。
周铁牛扔过来一套粗布衣裳,胸前的“宣府左卫朱印褪成了粉色,“先当队正,月饷五斗米——比在京里要饭强。
张铁柱凑过来,塞给他半块冷馍“兄弟,咱这行,活过三年才叫兵。
馍上沾着沙粒,贾珩咬了一口,硬得硌牙,却比荣国府的燕窝粥香。
末了的话夜渐深,风沙小了些。
贾珩躺在草席上,望着营盘外的星空。
黑子在马厩里打了个响鼻,像是在和他说话。
他摸出怀里的碎玉,月光下,“珩字泛着幽光。
远处传来巡夜的梆子声,“咚——咚——娘,他轻声说,“我活下来了。
周叔教了我好多——拉弓要稳,步战要狠,兵书要读进骨头里。
爹说得对,他是个好人。
风卷着沙粒掠过营盘,吹得草席簌簌作响。
贾珩裹紧号衣,想起周铁牛的话“活过三年才叫兵。
他攥紧碎玉,在心里说“我要活过三年,活过十年,活成您和爹盼的样子——护着宣府的风,护着宣府的百姓。
营盘外的胡杨在风沙里摇晃,像在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