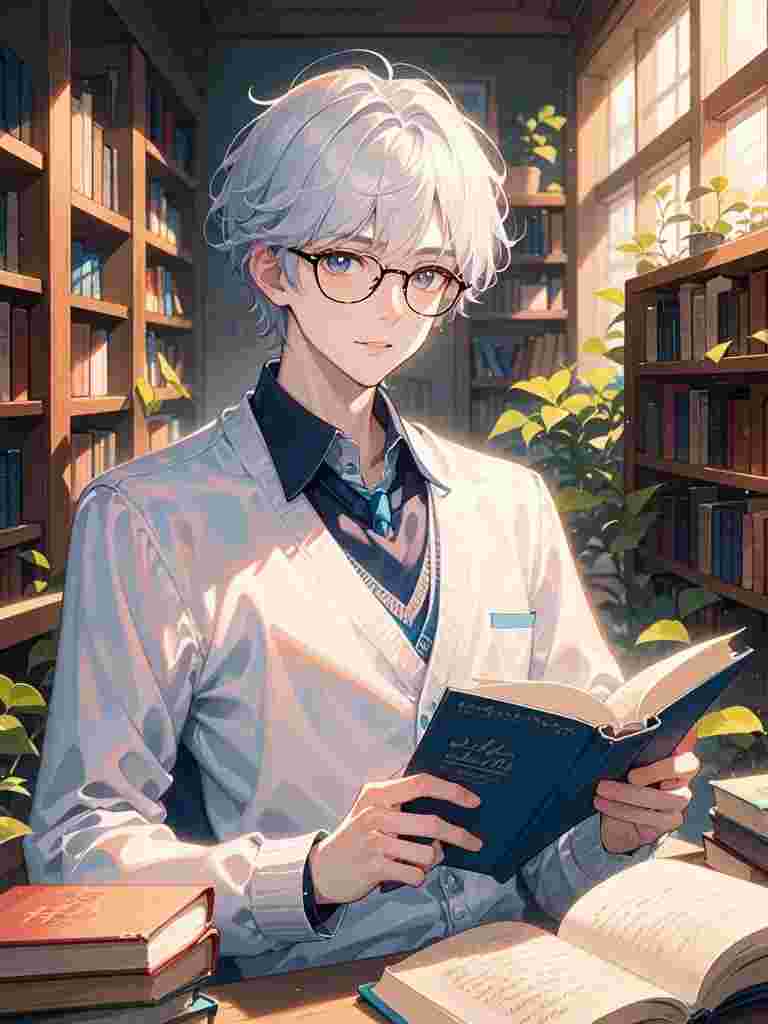第2章 送水
筒子楼里那点微薄的凉意在上午8点就被彻底蒸干。
阳光透过那扇形同虚设的窗,炙烤着铁皮屋顶,室内像个巨大的蒸笼。
汗水黏腻地贴在皮肤上,呼吸都带着灼热感。
我的采访也慢慢开展。
白天,我混迹在摇着蒲扇、抱怨拆迁款太低的老人堆里,坐在苍蝇乱飞、地面油腻的小吃摊前听老板骂骂咧咧地抱怨“保护费又涨了,或者在狭窄的棋牌室里,看那些眼神浑浊、叼着廉价烟的男人为几块钱的输赢争得面红耳赤。
我的采访本上,记满了这些琐碎的、充满烟火气的抱怨和叹息水压不稳、垃圾没人清、半夜楼下烧烤摊的噪音、小偷小摸越来越猖獗……这些都是民生痛点,是江涛和主编想要的“料,但总觉得隔靴搔痒,缺少一把能撬开这潭死水的锋利楔子。
那个地下拳场,像一个巨大的、散发着不祥气息的磁石,始终吸引着我。
我又去了两次,每次更谨慎。
我像一滴油混入沸腾的水,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观察,倾听,在震耳欲聋的喧嚣中捕捉那些零碎的、有用的信息碎片。
“妈的,黑皮那小子最近手真黑!
“听说‘老鬼’那边又塞了个新人过来,今晚‘试水’……周老板大气!
这场面,啧啧……放屁!
周正雄那老狐狸,钱都流他兜里了!
我们喝西北风?
“‘沙包’呢?
今天怎么没见?
又被‘黑皮’打废了?
“呵,那小子命硬,死不了!
在哪个犄角旮旯挺尸吧……沙包这个名字开始频繁地钻进我的耳朵。
在那些下注者、看客、甚至拳场内部人员的口中,它不是一个名字,更像一个代号,一个标签,代表着笼子里最底层的存在——专门用来消耗对手体力、供人取乐、甚至给某些特定人物“泄愤的活靶子。
赢?
对他们来说是奢望。
能活着从笼子里爬出来,就是胜利。
“听说昨晚‘沙包’又被‘疯狗’修理了?
那叫一个惨……骨头都断了吧?
真他妈抗揍!
“抗揍?
那是周老板‘照顾’他!
留着他这条贱命还有用呢!
零碎的信息拼凑出一个模糊而残酷的轮廓。
我本能地将这个名字和那个沉默的邻居联系起来。
他身上的伤,他眼中那片冰冷,他身上那种被生活反复碾压后沉淀下来的麻木与绝望……“咚咚咚!
敲门声粗暴地响起,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道,瞬间打断了我的思绪。
心猛地一跳。
会是谁?
房东昨天收了钱,按说不会这么快又来。
江涛知道我住这里,但他敲门不会这么凶。
我警惕地走到门边,隔着薄薄的铁门问“谁?
“送水的!
一个粗声粗气的男声,带着明显的不耐烦。
送水?
我昨天刚安顿好,根本还没订水。
一丝警觉爬上心头。
我凑近猫眼看到外面站着一个穿着脏兮兮蓝色工装的男人,身形壮硕,一脸横肉,肩上扛着一个巨大的、裹着塑料膜的桶装水。
他身后还隐约站着另一个穿着花衬衫、叼着烟的人影。
“我没订水。
我隔着门说。
“房东让送的!
赶紧开门!
沉死了!
工装男用脚踢了一下门板,发出哐当一声闷响,铁皮门都在震颤。
猫眼里,他身后的花衬衫男似乎朝这边瞥了一眼,眼神阴鸷。
我几乎可以肯定,这两人来者不善。
是在地下拳场被盯上了?
还是这地方本身就鱼龙混杂,被当成了新来的肥羊?
“我说了,我没订水。
你们找错门了。
我尽量让声音保持平稳,但心脏己经擂鼓般狂跳起来。
脑子里飞速盘算着这破铁皮门一脚就能踹开。
喊救命?
这筒子楼里人情冷漠,未必有人管。
报警?
远水救不了近火就在这紧张对峙的几秒钟,眼角的余光瞥见门外楼梯口方向的光线似乎晃动了一下。
一个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猫眼的视线边缘。
正是那晚蜷缩在拳场角落、满脸是血的拳手!
他换了一件同样看不出原色的旧T恤,洗得发白,肩头似乎还有个破洞。
额角的裂口被一块脏兮兮的、边缘泛黄的纱布草草盖着,但仍有暗红的血渍从边缘洇出来。
左眼依旧被凝固的血痂糊着大半,只留下那只右眼,此刻正扫视着门口的那两个不速之客。
他的出现毫无征兆,像一道突然投射下来的阴影。
扛水的工装男和花衬衫显然也察觉到了,同时转过头。
气氛瞬间凝固。
扛水的工装男眉头拧起,粗声粗气地呵斥“看什么看!
滚一边去!
花衬衫则眯起眼睛,上下打量着这个突然出现的、一身伤的瘦削青年,嘴角扯起一丝轻蔑的弧度,没说话,但那眼神里的威胁不言而喻。
青年没动。
他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自然垂在身侧。
那只完好的右眼,目光像冰冷的探针,缓慢地从工装男扛着的巨大水桶,移到他粗壮的脖颈,再滑向花衬衫叼着的烟头,最后定格在花衬衫插在裤兜里的那只手上——那只手的形状,明显握着什么东西。
他的视线最后落在我这扇紧闭的铁皮门上,停顿了极短暂的一瞬。
那眼神里没有任何情绪,没有同情,没有示意,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然后,他动了。
没有预兆,没有废话。
插在裤兜里的手闪电般抽出,带出一道冰冷的金属反光!
竟是一把磨得锃亮的、足有半臂长的沉重扳手!
动作快得只留下一道残影!
砰!!!
一声令人头皮炸裂的巨响!
沉重的扳手带着千钧之力,狠狠地砸在工装男扛着的巨大桶装水上!
塑料桶身瞬间炸裂!
巨大的冲击力让工装男猝不及防,被砸得猛地一个趔趄向后倒去!
桶里冰冷的纯净水如同决堤般狂泻而出,劈头盖脸浇了他一身,也瞬间漫湿了狭窄的楼道地面!
“我操——!
工装男惊怒交加的吼叫被水流声淹没。
花衬衫反应极快,在扳手砸下的瞬间,身体己经后撤,同时那只一首插在裤兜里的手猛地抽出——赫然握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弹簧刀!
他眼神凶狠,毫不犹豫地就朝那青年握着扳手的手臂刺去!
快!
狠!
准!
完全是搏斗拳击的亡命打法!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那青年仿佛早有预料。
砸裂水桶的扳手去势未弱,手腕猛地一翻,沉重的扳手借着惯性划出一个刁钻的弧线,带着风声,精准无比地磕向花衬衫持刀的手腕!
啪!
又是一声脆响!
弹簧刀脱手飞出,当啷一声掉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
花衬衫发出一声痛呼,捂着手腕踉跄后退,脸上瞬间褪去了血色,只剩下惊骇。
整个过程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从青年抽出扳手,到砸裂水桶、磕飞匕首,前后不过两三秒!
动作干脆、利落、凶狠!
带着一种常年挣扎在暴力边缘磨砺出的、近乎本能的精准和狠辣!
楼道里一片狼藉。
水流还在哗哗流淌。
工装男像只落汤鸡一样瘫坐在水里,惊魂未定。
花衬衫捂着手腕,死死盯着青年,眼神里充满了忌惮和怨毒,却再不敢上前一步。
青年站在原地,微微喘息着。
额角纱布边缘的血迹因为刚才的动作似乎又扩大了一点。
那只冰冷的右眼扫过两个狼狈的闯入者,然后,目光落在猫眼上。
我本能的身体往后一躲,仿佛他能透过猫眼看穿进来这一次,他开口了。
声音嘶哑,像砂纸摩擦着锈铁,没有任何起伏,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冰冷“滚。
工装男和花衬衫对视一眼,他们没敢再说一个字,甚至没去捡地上的弹簧刀。
工装男挣扎着爬起来,花衬衫也忍着痛,两人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地冲下楼梯,脚步声仓皇远去,留下满地的水和那个静静躺在水泊中的弹簧刀。
危机解除。
楼道里只剩下哗哗的水声,和一片死寂。
我背对着门,不敢再从猫眼里窥探。
背脊紧紧贴着冰冷的铁皮门,心脏还在狂跳,手心全是冷汗。
隔着门板,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外面那个人的存在。
他沉默着,没有离开。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胸腔里的惊悸,手指有些颤抖地摸向门锁。
咔哒一声,铁皮门被我拉开了一条缝隙。
楼道浑浊的光线涌了进来。
浓重的水腥气和淡淡的血腥味混杂着。
他就站在门外不到两米的地方,背对着我,微微低着头,似乎在看着地上那把寒光闪闪的弹簧刀。
那把沉重的扳手还握在他垂下的右手里,粗糙的木柄被他布满细小伤疤和老茧的手紧紧攥着,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湿透的旧T恤贴在他瘦削的背上,勾勒出清晰的、微微起伏的肩胛骨轮廓。
额角纱布上的血渍在光线中显得格外刺眼。
水流漫过他的旧帆布鞋鞋面,他似乎毫无察觉。
听到开门声,他的身体极其轻微地顿了一下,却没有回头。
空气仿佛凝固了。
只有水流声单调地响着。
“……谢谢。
我的声音有些干涩,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沉默。
他终于缓缓转过身。
那张脸完全暴露在光线里。
额头的伤口比昨晚看起来更清晰,纱布盖不住的地方皮肉肿胀外翻,边缘是暗红的血痂。
糊住左眼的血污被水冲淡了一些,但睫毛上还凝结着暗红色的块状物。
右眼是唯一清晰的窗口,此刻正抬起来,看向我。
没有了昨晚在拳场灯光和烟雾中的那种穿透一切的锐利和专注。
此刻的眼神,更像一片结了冰的荒原。
疲惫,空洞,深不见底。
里面翻涌着的东西太过复杂,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有挥之不去的痛楚,有深入骨髓的麻木,还有一种近乎绝望的厌倦。
仿佛刚才那雷霆般的出手,只是他日复一日挣扎求生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令他无比厌烦的插曲。
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大约两秒。
那两秒里,没有任何情绪波动,没有好奇,没有探究,甚至没有一丝一毫“被感谢后应有的反应。
就像看一件毫无意义的物品。
然后,那目光移开了。
他什么也没说,仿佛刚才那一声“谢谢只是空气的振动。
他弯下腰,伸出那只没有握扳手的手——那只手的手背上也布满了细小的划痕和青紫——捡起了地上那把冰冷的弹簧刀。
动作很随意,仿佛只是捡起一块路边的石头。
他首起身,依旧没有再看我一眼,握着扳手和匕首,沉默地转过身,踩着漫过脚踝的积水,一步一步,走向楼梯口。
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响,沉重而疲惫。
湿透的鞋底踩在水泥地上,发出黏腻的“吧唧声。
他微跛着,左腿似乎有些不便,每一步都牵扯着某种隐痛。
那道沉默、单薄、带着一身新旧伤痕的背影,就这样消失在楼梯的阴影里。
楼道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敞开的门边,看着满地狼藉的冰冷水流,还有空气中弥漫的、混杂着水腥、血腥和暴戾余韵的气息。
心脏深处,除了后怕,还有一种更沉、更冷的情绪在缓缓弥漫开。
我蹲下身,手指有些发凉,小心翼翼地捡起飘到门边的一张泡湿的纸片。
那是刚才混乱中从采访本里掉出来的速写,画着一个模糊的、蜷缩在阴影里的身影。
墨水被水洇开,那身影变得越发模糊不清,只有额角一道暗红的印记,在湿透的纸面上晕染开来,像一道永不愈合的伤口。
我很清楚他不是英雄,更像一头被逼到绝境、伤痕累累、随时会反噬的困兽。
而我和他之间,正在踏入同一条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