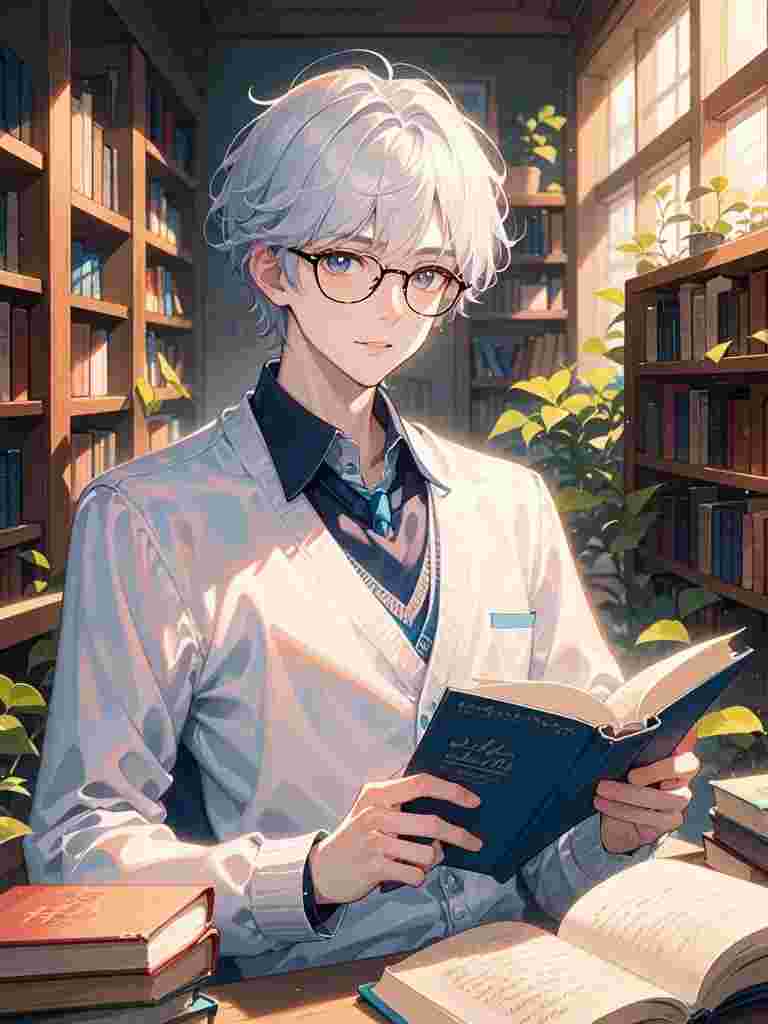第9章
一周后,爷爷带了位穿白大褂的年轻人来病房。
“这是顾晏,我在哈佛的学生,专攻神经修复。
爷爷拍着他的肩膀,“你这双手,得让最懂的人来治。
顾晏的指尖带着消毒水的清冽,检查断手时动作轻得像怕碰碎瓷器。
“温小姐的肌腱缝合很专业,他抬眸时眼里带着笑意,“看来家学渊源不是空谈。
我扯了扯嘴角,没接话。
康复训练比想象中更疼。
顾晏总在我疼得攥紧床单时,递来颗水果糖“当年我给兔子做神经吻合术,手抖得比你现在还厉害。
他说起在实验室的糗事,声音像温水漫过石子,“后来发现,越怕疼,越握不住手术刀。
我盯着他手里的康复球,突然想起第一次为逝者化妆,爷爷说“手要稳,心要静。
那时的我不懂,原来心死过一次,手也会跟着失去力气。
三个月后,顾晏把支画笔塞进我手里。
“试试?
他铺开画纸,上面是他偷偷画的病房窗台,雏菊开得正好,“爷爷说你小时候最会画这个。
笔尖触到纸面的瞬间,我像被烫到般缩回手。
断指的关节传来钝痛,那些在殡仪馆握着化妆刷的日夜,突然变成扎人的碎片。
“不想画就不画。
顾晏把画笔收起来,“我带了新的康复方案,今天练握力球就好。
可那天晚上,我还是偷偷摸出了画笔。
月光透过窗户落在纸上,我画了个模糊的小人,坐在冰柜里,外面是无尽的黑。
顾晏端着热牛奶进来,没说话,只是帮我把台灯调亮了些。
“其实,我盯着画纸上歪歪扭扭的线条,“我不想再碰遗体了。
那些冰冷的皮肤,缝合时的触感,总让我想起自己躺在手术台上的瞬间。
鬼门关前走过一遭,才懂活着有多金贵。
顾晏放下牛奶杯“那就不碰。
他指着窗外的梧桐树,“你看这叶子,春天发芽,秋天落叶,和人一样有生命周期。
画活的东西,或许更有意思。
半年后,我的右手能稳稳握住画笔了。
顾晏帮我联系了家画廊,第一次展出的画里,全是阳光下的花草、奔跑的孩子、街角的咖啡馆。
有幅画叫《重生》,画的是冰柜里伸出只手,指尖触到了外面的光。
开幕式那天,爷爷拄着拐杖站在画前,眼眶又红了。
顾晏站在我身边,递来杯温水“他们说你画风里有种温柔的韧性。
我望着人群里那些陌生的笑脸,突然觉得,不用再为逝者缝补遗憾,能为活着的人画下阳光,也是种不错的活法。
断手还会在阴雨天发疼,但握画笔时的震颤,再也不是因为恐惧。
完全康复的第二年,顾晏向我求婚了。
我们在爷爷的见证下举行了婚礼,他很温柔,凡是都会以我优先,爷爷说,只有这样的男人才值得托付终身。
至于沈墨言,听说他在牢里总对着墙壁画画,画的全是安宁殡仪馆的白菊。
但这些,都和我没关系了。
我的手下,从此只有生,没有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