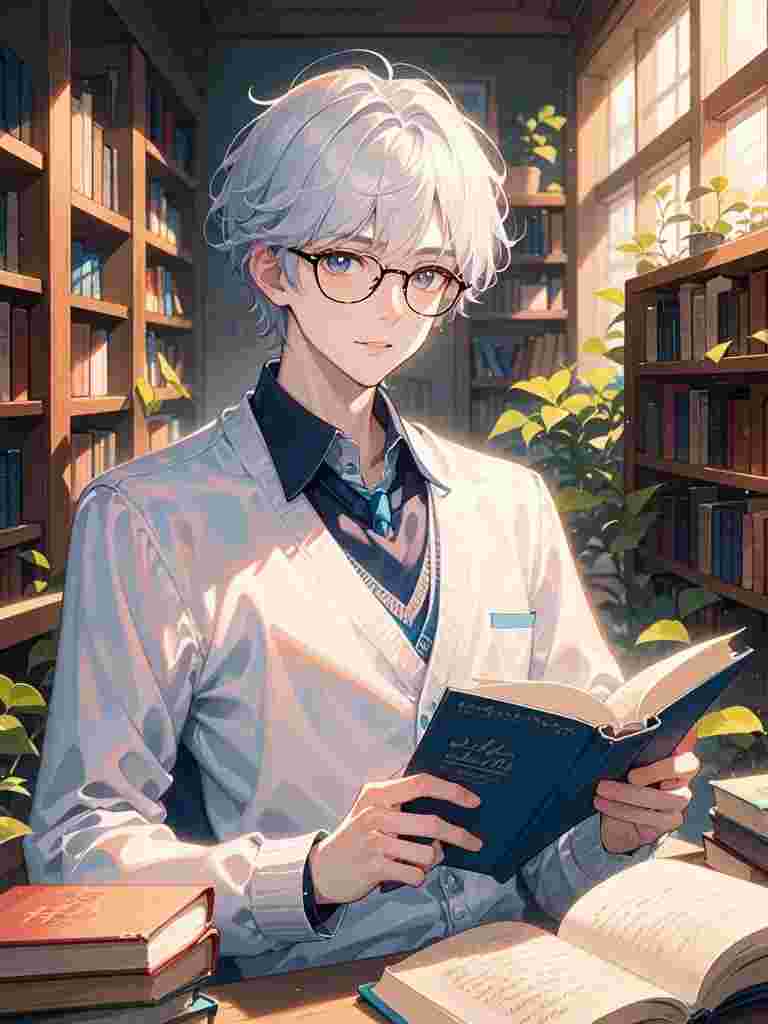第5章
阮时宴猛地瞪大了眼,嘶吼出声“姜闫书,你敢!
话音未落,两个保镖已如铁塔般逼近,死死攥住他的手腕,像两把冰冷的铁钳。
其中一人抓着他的手,高高扬起,朝着他自己的脸,狠狠扇了下去!
啪!
一声脆响,清脆得刺耳。
阮时宴的大脑一片空白,耳中只剩下尖锐的嗡鸣。
他没有看任何人,目光穿过层层阻碍,死死钉在沈清歌那张毫无波澜的脸上。
她曾笑着对他说“时宴,别怕,我护着你,一辈子。
幻影与现实重叠,然后被下一声脆响彻底击碎。
啪!啪!啪!
沈清歌甚至没有看他,只是空洞地望着前方,嘴里机械地报着数。
“三。
“四。
……
她像一个最公正的裁判,用数字,将他的尊严一寸寸碾碎。
直到第九十九下落下。
阮时宴的半边脸已经没了知觉,嘴角撕裂,满口都是温热的铁锈味。
姜闫书唇角噙着快意的浅笑,别过脸去,仿佛于心不忍。
沈清歌这才挥了挥手。
保镖松开手。
阮时宴像一滩烂泥,狼狈地摔在地上。
屈辱的眼泪混合着血珠,一颗一颗,砸进冰冷的尘土里。
一双昂贵的公主鞋停在他面前。
沈清歌蹲了下来。
她伸出冰冷修长的手指,想去碰他脸上的血污,像在安抚一只不听话的宠物。
“不乖,打。
她顿了顿,用一种天真又残忍的语气补充。
“乖,就,不打。
阮时宴用尽全身力气,抬起头,狠狠拍开她的手。
“滚!
沈清歌看着自己被打开的手,眸子暗沉了一瞬,随即缓缓站起身,唇角勾起一个冰冷的、毫无笑意的弧度。
她走到姜闫书身边,当着阮时宴的面,在他唇上印下一个缠绵的吻,像是在宣告所有权。
“闫书,回,家。
汽车的引擎声轰鸣着远去,两点猩红的尾灯,像恶魔的眼睛,消失在夜色里。
她没给他留一辆车。
阮时宴回到那栋曾被他称为“家的别墅时,已是半夜。
二楼的主卧,灯火通明。
窗帘上,映着两具剪影。
他不想看。
可那压抑的喘息和婉转的吟哦,却像一把淬毒的刀,一刀一刀,凌迟着他的神经。
阮时宴在冰冷的夜风中,站成了一座没有灵魂的冰雕。
直到天光破晓。
里面的声音终于停歇,他才推开了那扇沉重的门。
玄关一片狼藉。
他送她的羊绒围巾被撕碎了,踩在脚下,碾进污秽里。
黄花梨木的玄关柜上,赫然摆着一个炫耀战利品般的避孕套空盒。
他只想逃。
一个慵懒又带着情欲沙哑的声音,却从楼梯上传来。
姜闫书只披着一件宽大的丝绸睡袍,慵懒地倚在扶手上,衣襟大敞,露出喉结上暧昧的红痕。
他轻叹一口气,眼神里是淬了毒的怜悯。
“你还不知道吧,清歌她一个月前就申请跟你离婚了。
“今天啊,可是我们领证的好日子呢。
他缓缓走下几步,停在阮时宴的面前。
拿出两本崭新的、刺眼的红本子,像丢垃圾一样,轻飘飘地拍在阮时宴的胸口。
“阮时宴,如今我才是,沈清歌名正言顺的丈夫。
他凑到他耳边,用情人般呢喃的语调,说出最恶毒的话。
“你怎么就不明白,爱情里不分先来后到。
“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
阮时宴看着那两本结婚证,心脏像是被那抹红色灼出一个滚烫的洞。
他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局。
可亲眼看见,又是另一回事。
他忽然笑了,抬起眼,眼底是烧尽一切后的灰烬。
“你喜欢这些歪理邪说就自己实践,别来跟我沾边。
“好啊,时宴哥哥。
姜闫书凑得更近了一些,笑得轻佻又恶毒。
“那我就实践一下,给你看。
话音未落,他往后一靠,滚下了楼梯。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