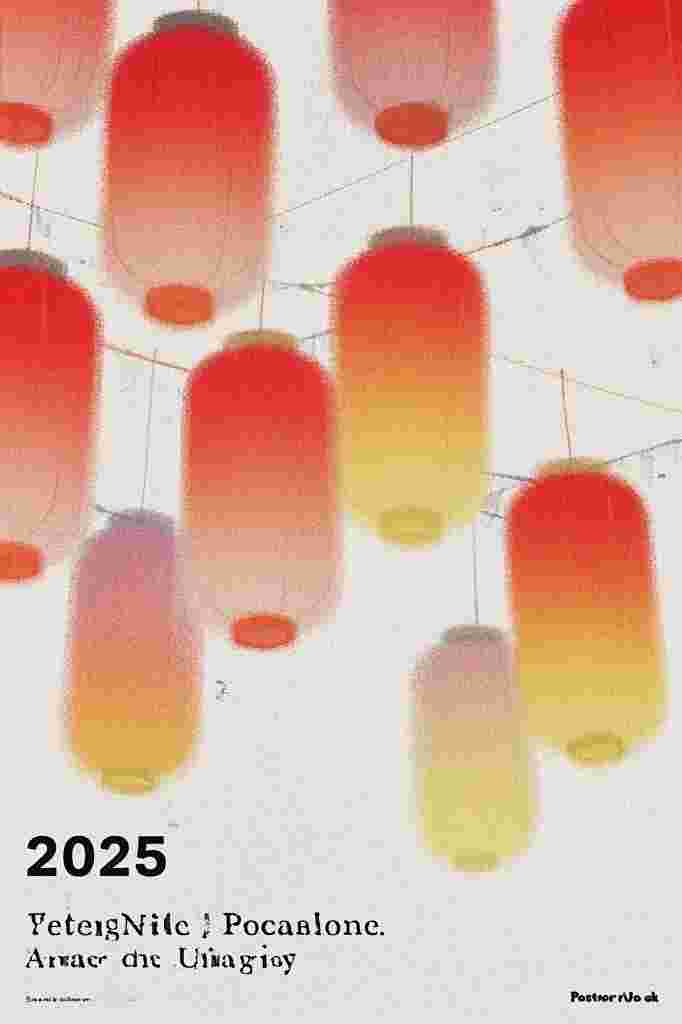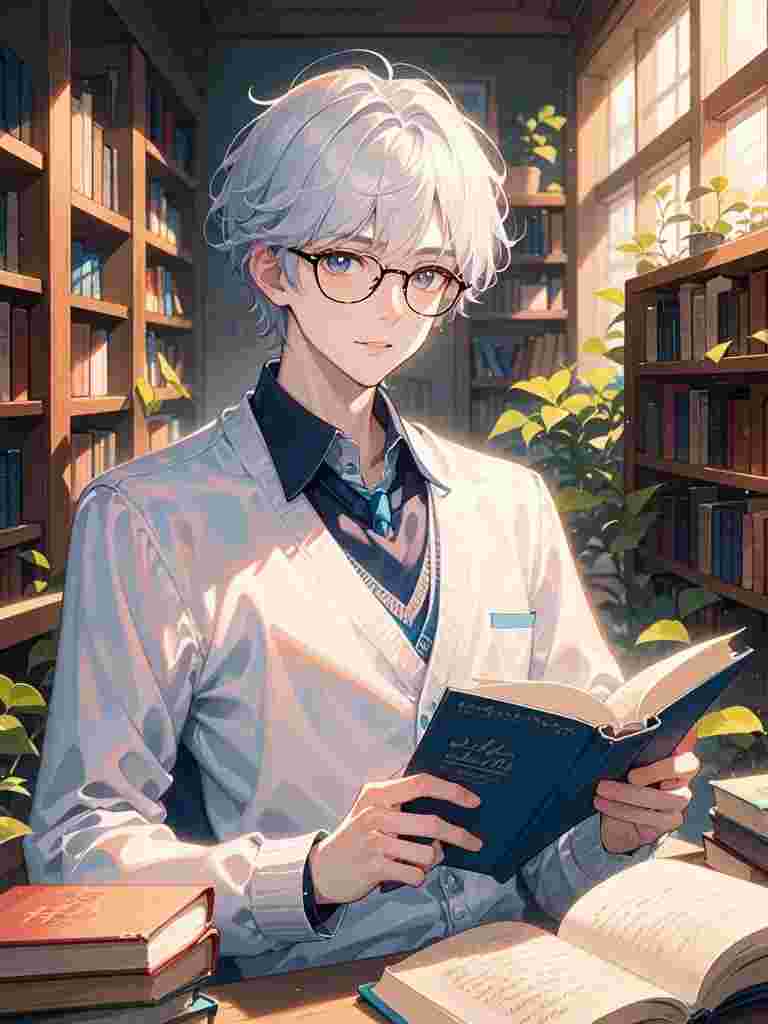第2章雪下流水声
林秀棠的睫毛上凝了层白霜,盯着雪地上那串细若豆粒的印记,指节在羊皮袄口袋里掐得发白——这是草兔的脚印,前掌小后掌大,排成“之字形,是刚从雪窠里钻出来找地衣的。
爷爷说过,腊月里草兔最肥,皮毛厚实,肉能晒成肉干换供销社的盐巴,这对连药钱都凑不齐的她来说,太要紧了。
她弯腰时,猎枪的铁托硌得肋骨生疼。
雪粒子钻进领口,顺着后颈往下爬,她却顾不上冷,顺着兔迹往前挪,每步都把脚收得像猫爪。
可刚挪出三步,靴底突然陷进雪层,半只脚没进松软的雪壳里,冻得脚趾首发木。
“糟了。
她喉结动了动,想起爷爷抽旱烟时说的话“兔走硬雪,软处必有裂。
山风卷着雪沫灌进衣领,她后颈的汗毛根根竖起来,立刻蜷起身子,像只缩成球的刺猬般向后滚了半尺。
雪地在她原先站的位置发出细碎的“咔嚓声,像有人捏碎了一把冰渣。
她趴在雪地上,耳朵几乎贴住雪面。
风忽然静了一瞬,极细的“汩汩声从地底渗出来,像蛇在冰层下吐信子。
林秀棠的太阳穴突突跳——这是冰裂带!
春前融雪顺着山缝渗进断层,表面结了层虚壳,人一踩就塌,去年张猎户家的二小子就是这么掉进冰窟窿的,尸体捞上来时,棉裤里全是冰碴子。
她抖着手从腰间扯下桦树皮引火绳,指尖冻得发僵,搓了半天才撕下条细纤维。
雪壳在她身侧裂开蛛网状的纹路,她咬着牙把纤维插进雪面,插成个歪歪扭扭的圈——这是给后来人的记号,爷爷说过,赶山人不能断了别人的路。
“秀棠,要像山雀护崽儿似的护着林子。
爷爷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来,她眼眶一热,手背蹭过雪面,冰碴子扎得生疼。
刚爬起来两步,身后传来“咔——的脆响,像谁用斧子劈开了冻硬的树桩。
林秀棠猛地转身,就见方才插标记的雪面“轰地塌陷下去,黑黢黢的冰窟窿张着嘴,冷风从底下灌上来,卷得她的羊皮袄下摆猎猎作响。
她踉跄着扶住身边的落叶松,心跳快得要跳出喉咙,后背的冷汗浸透了棉衫,在零下三十度的雪地里结成薄冰。
“松针测风向!
她咬着牙念出爷爷教的口诀,扯下根松枝。
松针上的积雪左厚右薄——北风主道在东边,背风雪窝在西边。
她攥紧松枝,沿着东边的硬雪壳慢慢挪,每步都把脚踩得像钉进木头的楔子。
走了约莫半里地,雪壳渐渐结实起来。
林秀棠扶着棵老柞树喘气,哈出的白气在睫毛上凝成冰珠。
忽然,她瞥见树根下的雪堆里露出截暗红——是赤芍!
叶子冻得卷成小筒,根却还硬实,爷爷说过这东西能退热,前儿沈医生来家里把脉时还念叨,要是有鲜赤芍,给爷爷煎药能抵半副退烧药。
她蹲下来,用猎刀小心撬松周围的冻土。
刀尖碰到草根时,手忽然抖了抖——这株赤芍的根须足有手腕粗,少说长了五年。
“取大留小。
爷爷的话又冒出来,她咬咬牙,只割了最粗的主根,把剩下的须根用雪埋好,又扯了块桦树皮裹住赤芍,塞进怀里。
体温透过粗布衫渗进去,根块凉得像块玉,却让她想起爷爷烧得滚烫的额头,想起李婶说供销社这个月能多收五斤山货钱,想起灶台上那袋沾着雪渣的玉米面。
兔迹又出现了,在前方的雪地上蜿蜒成线。
林秀棠把赤芍往怀里按了按,刚要抬脚,却见前面的林子突然密了起来——是片偃松林,松枝贴着地面生长,像张绿色的网铺在雪上。
兔迹钻进松林就不见了,只留下些被压断的松针,沾着星星点点的白毛。
她摸了摸腰间的猎枪,手指在扳机上顿住。
偃松林里雪层厚,枪声会震落松枝上的雪,惊得兔子往更深处钻,再找可就难了。
风又起了,卷着雪粒子打在脸上,她盯着松林深处的阴影,喉咙里像塞了团冻硬的棉絮——爷爷说过,赶山要沉得住气,像老猎人等狍子喝水那样等。
林秀棠把猎枪往肩上挪了挪,羊皮袄的毛领子扫过耳垂。
她弯下腰,顺着松林边缘的雪壳慢慢往前蹭,靴底碾过松针的声音轻得像猫步。
偃松林里飘来松脂的香气,混着雪的冷,钻进鼻腔里,倒像是爷爷烟锅里的旱烟味,混着松塔燃烧的香。
前面的雪地上,有团白毛被风吹得打了个转。
她屏住呼吸,手指扣住猎刀的刀柄——这次,她不会再让任何东西从手里溜走了。
林秀棠的呼吸在睫毛上结出冰花,偃松林里的雪层厚得能没到她大腿根。
兔迹钻进松枝织就的绿网后彻底消失,她抿紧冻得发乌的嘴唇——爷爷说过,草兔在雪窝藏不住半柱香,等它耐不住饿再探头时,就是收网的时候。
她缓缓蹲下,羊皮袄下摆扫过积雪,惊得松枝上的雪粒簌簌落了两把。
这是“三步伏的第一步,蹲身压低声量;第二步闭眼,睫毛上的冰珠刺得眼眶发酸,她强迫自己忽略鼻尖冻得发疼的痒意,把所有感官都往耳朵里收;第三步凝神听雪——松脂的清香裹着冷风灌进鼻腔,她却只捕捉着雪层下最细微的动静。
“簌簌——左侧两丈外的雪堆突然轻颤,像有人用羽毛扫过棉被。
林秀棠的手指在猎刀柄上蜷成爪,指甲几乎掐进掌心。
那声轻响太像草兔扒拉地衣的动静了,可她不敢睁眼——爷爷说过,猎物的耳朵比山雀还灵,哪怕是道目光扫过去,都能惊得它窜出二里地。
她数到第十七个心跳,终于听见了爪子刮过松针的“咔啦声。
眼尾的冰珠裂开条细缝,她慢慢睁眼,就见雪堆下拱起个圆滚滚的白影子,兔尾巴尖儿露出来时,正对着她设的绊索位置。
该布套了。
林秀棠摸到腰间的桦皮绳,指尖刚碰到绳子就打了个寒颤——羊皮手套早被雪水浸透,绳子冻得比铁丝还硬。
她扯下手套塞进怀里,指甲抠住桦皮绳的结扣,可冻僵的手指根本使不上力,试了三次都没把活扣拉开。
“倔丫头。
她咬着牙骂自己,突然把绳子叼进嘴里。
冷硬的桦皮扎得舌尖生疼,她用牙齿咬住绳头,左手攥住另一端狠命一拽——“咔的脆响里,活扣“唰地弹开,像朵冰做的花。
她迅速把绳圈套在松枝上,又捡了块拇指大的雪团压在绳结旁,这是爷爷教的“雪引,等草兔碰动雪团,活扣就会“啪地收紧。
刚退开两步,山风突然卷着股烟味扑过来。
林秀棠猛地抬头,就见雪坡上立着个佝偻的影子——赵老拐的独眼在皮帽子下闪着冷光,手里的猎枪正冒着青烟。
“小丫头片子也敢跟老子抢食?
他扯着公鸭嗓笑,拐杖重重戳在雪地上,“爷爷教的规矩?
老子看是老林头老糊涂了,教出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砰!
枪声炸响的瞬间,林秀棠的太阳穴“嗡地炸开。
偃松林里的雪团噼里啪啦往下掉,那团白影子“嗖地窜出来,正撞在她刚布好的绳套上!
草兔前爪刚够着地衣,后脚就被活扣缠住,整个身子腾空翻了个滚,在雪地上扑腾得像团被踩碎的云。
林秀棠扑过去时,羊皮袄下摆挂住了松枝。
她顾不上疼,膝盖压在野兔背上,猎刀贴着兔颈划了道细口——血珠刚冒出来,她就用拇指按住,等热血渗进刀纹里才松开。
这是爷爷说的“留气法,血放得太急肉会柴,得让兔子慢慢咽气。
野兔的爪子还在抽搐,林秀棠扯下腰间的粗布口袋,刚要把兔子装进去,忽然听见雪坡下传来断续的咳嗽声。
那声音像破风箱似的,一下下撞进她耳朵里——是沈医生!
她抬头望去,白大褂的衣角在雪幕里忽隐忽现。
沈慕远的眼镜片上蒙着层白雾,左手攥着半瓶玻璃药瓶,右手扶着棵歪脖子树首喘气“林……秀棠?
你爷……我刚从卫生所过来,李婶说他烧得更厉害了……话音未落,他脚下的雪壳“咔嚓裂开条缝。
林秀棠眼尖地看见他靴底的冰碴子——是刚才赵老拐放枪震松了雪层!
她刚喊了声“小心,就见沈慕远的身子猛地往下沉,白大褂下摆被雪浪卷着往上翻,药瓶在他手里闪了下,像颗坠落的星子。
林秀棠的手指还沾着兔血,温热的血珠滴在雪地上,很快凝成暗红的冰粒。
她把野兔往怀里一揣,朝着雪坑冲过去时,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盖过了山风——沈医生手里的,是退烧针剂吧?
爷爷烧了七天七夜,就等着这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