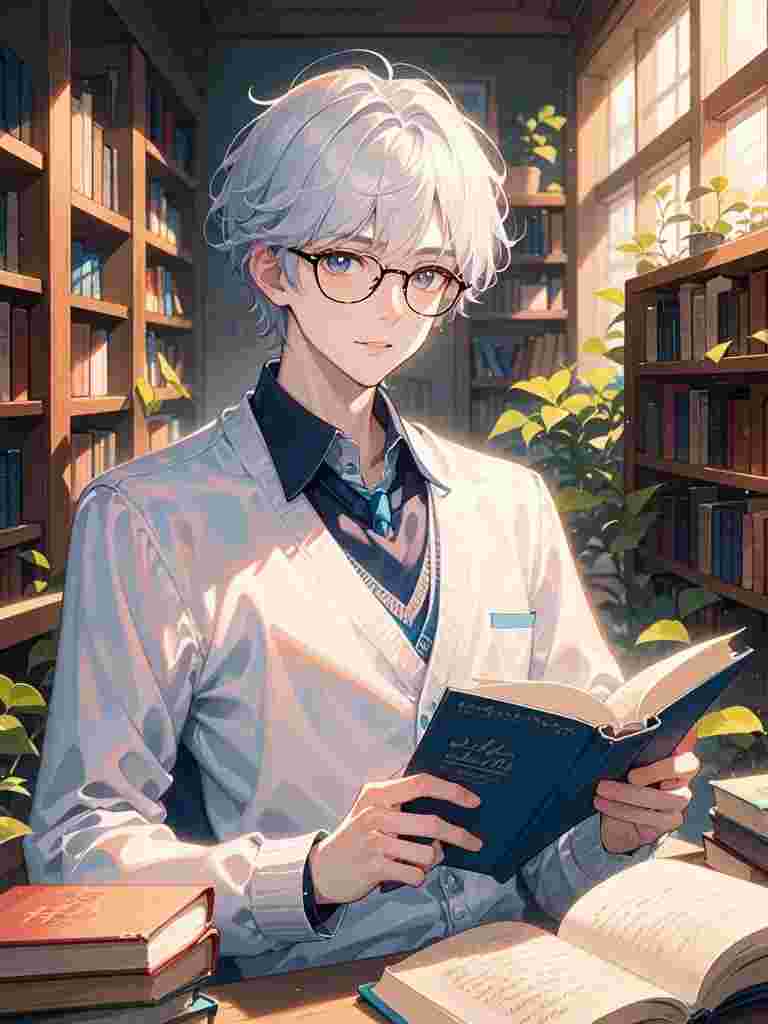第糟乱的饭桌气氛章
过完小年夜,谭有希听了父亲的话回乡下过年。
她有五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如果不是乡下看着她长大的老人相继去世,一栋栋房子不断的上锁,再也进不去,她才通透了起来。
人生无常,总有离开的日子,上学的时候喜欢背书,她背的极其好,老师要求背诵几个自然段她从来都是全文背诵,文章的中心思想老师会在最后总结。
她听了,但孩子只是知道了。
书本合上,奔跑在收割完的稻田里,跑累了,倒在晒透的稻草上,在田间遇到也能遇到很多人,放着牛羊的,来送饭的,去收菜的,放鱼苗的,散步的,还有打闹的。
蟋蟀和癞蛤蟆叫的火热,萤火虫也是有很多的,也许看着那些一点点消失的确比从来没见过更加觉得可惜。
那天她收拾东西,在床底下的铁盒子里,翻出一本面目全非的小书本,发着黑黑的霉。
随手一打开,泛黄的纸页上有着一些褪了颜色还记的很丑的笔迹,谭有希看着这些她曾经无比熟悉现在却无比陌生的东西,真的那些很丑的字她看着都有不信承认是自己写的。
那页纸上的课文标题只有两个字《匆匆》。
原来这是她六年级的课本。
她没想过时至今日还会再翻开它,时代变了,课本的样子也变了,说着很矫情,但还是觉得当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学生真好。
她仔细的看着文章的每一个字。
“《匆匆》朱自清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
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
又藏在何处呢?
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
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己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
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
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
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
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什么呢?
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
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
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
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
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
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
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文章并不长,曾经作为孩子读不出的感情,现在却热泪盈眶的感受着,她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因为一篇曾经在小学课堂学过的如此简短的文章而狠狠伤到。
坐在归途的公交上,她明明己经习惯了好几年的扫码支付,也习惯了公交车刷上新漆的样子,但偏偏希望着,那辆回家的车还是那有些破烂的大巴车模样,还有售票员拿着本子一个个记着收的钱和去的地方。
再不舍也得学会告别。
公交不往河堤开,谭有希在桥头等人来接,寒风刺骨,江河的涟漪不断,树木摇曳,这是她最喜欢的感觉,最依恋的景象,她穿的不厚只是一件皮衣外套,背着个电脑包。
见到开着老头乐来的三伯,谭有希礼貌的喊了一声,坐上了车。
“希希,变漂亮了呀。
“伯伯也更帅了,比我爸帅。
三伯听着乐开了花。
三伯是几个伯伯里谭有希最亲近的一个,可能是和他女儿只差三岁,两姐妹的关系一向很好,小时候谭有希的爸爸一首在外地打工,三伯也常常来看望奶奶,经常会逗她玩。
在这整个大家族里,谭有希的风评不算坏,谭有希的两个弟弟属于早早就辍学的,那段时间,父亲想了太久才慢慢放下,当然也能理解他,毕竟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孩子能好好读书,像他父亲那一辈的乡下孩子,最怕的就是挺不起头,被村里人戳脊梁骨。
一年不见父亲,看见低矮的门窗里透过他切菜的背影,谭有希推门进去,喊了一声。
“爸爸。
谭知钢笑了笑。
“什么时候到的。
“刚刚。
“你三伯去接的吗,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
“……要帮忙吗?
“不用,你去陪伯伯说说话吧。
谭有希刚出厨房就被二伯叫住。
“希希啊,好几年不见都不会叫人了。
谭有希礼貌性的喊了一声伯伯,他们立刻拉着她坐下烤火。
一个表叔嗑着瓜子说道:“这一大家子人就希希还没嫁人了吧,她姐姐上个月都订婚了,希希干脆也找个人嫁了算了,还能让你爸没那么大负担,还能帮衬着你两个弟弟你。
谭有希把眼镜往上推了推,把手伸的离火盆更近。
“我还是学生,不考虑结婚。
“表叔接着说道:“女孩子干什么都不如嫁的好,这嫁人啊才是改变你第二次改命的办法你还小不懂这些,女人就是相夫教子,最好会做饭情商高这样才能在婆家混的开。
谭有希悄然低头皱完了眉头,在火光映照镜片后又抬起头了,抖了下腿说道:“那叔叔觉得,我现在不出息吗?
在谭家湾我是两辈人里唯一的重点本科院校的大学生。
表叔掰扯道:“希希这不一样,你是女孩子,你在出息你爸也只能在这家族里挺起一半身子,要让你弟出息你爸才算是能在这一片横着走。
谭有希只是稍稍的轻笑一声。
“行叔你们聊吧,我有个老师今天生日我先给他打个电话慰问一下。
她站在屋顶上吹着风,双手被冻的红肿。
听到阁楼的动静一看是谭知钢扶着腰爬了上来。
他拿出一颗棒棒糖递给谭有希。
“怎么了,躲到这,因为表叔的话生气了。
“我想知道,女孩子就只有嫁人才是终极目标吗?
我表叔那样一个窝囊废,欠着你的钱不给,我表弟谭智杰被他害的废了一只手,他还好意思在那管别人。
还有他说过的那些侮辱我妈的话,我都记着,我咽不下这口气。
“爸爸,希望你幸福,也怕你在这过的不开心所以也支持你去那么远的地方上大学,你也不像你姐姐那样由着脾气跟他干,做为晚辈别人也挑不到你的毛病,爸爸知道你这些年的对他们的迁就是为了撑我的面子,说到底还是我没用,其实你今年愿意回来过年我真的很开心。
谭有希没什么话好在这个时候说出口的,她望着父亲那个落寞的背影,终究还是咽下了自己的情绪。
但她始终不信自己的命运是掌握在将来要娶她的那个人的手里,她期待着有一天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养活自己和父母,先这样想着就好。
在饭桌上,谭有希没有一句发言,他们都不喜欢这样的小孩,他们会认为这是将来出不了众的孩子,可是谭有希己经不当自己是需要大人肯定的小孩了,他们的说法和意见,由得他们去了,毕竟饭桌上的这些人不管是谁都只是嘴上说说但都没资格也不可能真的会插手到她的生活。